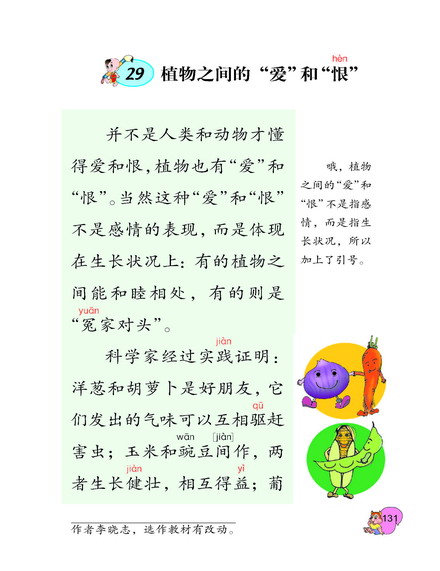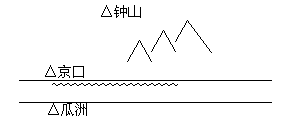作者:普里什文(普里希文)简介
冀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又名普里希文,1873-1954)是20世纪苏联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人物。世纪之初,他是作为怀有强烈宇宙感的诗人,具有倾听鸟兽之语、草虫之音异能的学者,步入俄罗斯文坛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虽历经俄罗斯文学发展历程中批判现实主义的衰落、现代主义的崛起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繁盛,却始终保持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不仅拓宽了俄罗斯现代散文的主题范围,而且为其奠定了一种原初意义上的风貌。
英文名称:MikhailMikhailovichPristinaMan
1873年1月23日(新历2月4日),普里什文出生于苏联奥廖尔省叶列茨县一个破败的商人、地主家庭,童年时代在接近自然世界的乡村度过。他的青少年岁月经历了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思潮的洗礼,还在上中学时就对当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兴趣。1894年他考入拉脱维亚里加综合技术学校,不久开始翻译德国革命家倍倍尔的作品,1897年因传播马克思主义被捕入狱。出狱后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攻读农艺学。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了斯宾诺莎、康德、尼采和歌德的著作。1902年回国,开始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克林和卢加地区做农艺师,后受著名民俗学家翁丘科夫委派,到当时很少有人研究的俄罗斯北方白海沿岸的密林和沼泽地带进行地理和人文考察,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民间文学作品。他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角度,对当地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根据考察见闻,写成随笔集《飞鸟不惊的地方》,以富有民间文学特色的语言,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该地区的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观,描述了尚未被现代文明冲击的农民、渔夫、猎人、妇女和儿童的淳朴生活和风俗习惯,并且寻幽探秘,追寻当地文化和分裂教派传统汇集而成的独特地域文化,融合了从历史深处延宕而来的凝重而从容的思考。《飞》的成功使普里什文在俄罗斯文坛崭露头角。
在以后的10多年中,普里什文的多数时间都在路途、山水中度过,行吟漫游成为他一系列探求的开端。在此期间,他又写了《跟随神奇的小圆面包》(1908)、《在隐没之城的墙边》(1909)、《黑阿拉伯人》(1910)等随笔集,分别记述自己的几次旅行经历。在二三十年代,普里什文相继推出自传体长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1923-1954)、随笔集《别列捷伊之泉》(1925-1926)、《大自然的日历》(1925-1935)、《仙鹤的故乡》(1929)、中篇小说《人参》(1933)等,这些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普里什文创作风格日臻成熟,尤其是《别列捷伊之泉》,更具转折意义。不仅标志着普里什文“自然与人”创作思想的生成,而且最终使他为年轻的苏维埃文学所接纳。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按照自然的时间推进,并应和于自然界的种种变化,从春天的第一滴水写起,直至人的春天,其间穿插着俄罗斯中部乡村的打猎、农事、节庆等生活细节。在这里,普里什文不仅把自然与具体的日常生活,与人的复杂情感结合起来,而且第一次把“大地本身”当作“故事的主人公”。这表明,在普里什文那里,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生存的外在环境,不再是存在于人之外的特异的东西,它就具体地贯穿于生命活动和生活进程中,成为一种深入人的实际生活和具体进行在人内心世界中的过程。四、五十年代是普里什文创作的全盛时期,《没有披上绿装的春天》(1940)、《叶芹草》(1940)、《林中水滴》(1943)、《太阳宝库》(1945)、《大地的眼睛》(1946-1950)、《船木松林》(1954)和未完成的《国家大道》都为作家带来更广泛的声誉。他的作品《林中小溪》被选入苏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书。1954年,普里什文卒于莫斯科近郊的林中别墅。
普里什文不俗的文学成就使他有理由被俄罗斯文学界和读者推为名家。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莫斯科文艺出版社曾分别出版他的6卷集和8卷集,至于作品的单行本也是不断再版。根据近期资料,1999年“竹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林帐》,2000年“行动出版社”在“经典荟萃”系列丛书中将他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中短篇作品结集出版,“蜻蜓新闻出版社”再版了《孩子与鸭子》,2001年“奥林巴斯行动”、“卡拉普斯”、“探索者世界”、“儿童文学”等几家出版社分别重印了作家的《太阳宝库》、《刺猬的故事》等,“国家出版社”也出版了普里什文新选集的前两册。此外,从1998年至今,至少已有19种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籍中收入了普里什文的散篇作品,这些书籍的总发行量已超过33万册。他时而作为民间故事的写作者与克雷洛夫、托尔斯泰等人并列齐名,时而又作为描写俄罗斯自然的圣手与普希金、屠格涅夫、费特等人同时出现,时而他还作为著名的儿童作家被列入马克·吐温、罗大里一类。
表面上看,俄罗斯人一直在读普里什文,即便在市场化、商品化的新俄罗斯时代,人们对他的兴趣似乎也并没有明显衰减,然而就是在这一片出版热潮的背后,普里什文的文学意义实际上却在悲剧性地被淡忘和湮没。从当下普里什文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定位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的文学和精神意义都被大大贬低,他创作中的儿童视角被狭义的儿童文学所取代(上文所列新版书几乎都属于“中小学生文库”、“儿童经典”系列),以至于再版的作品只集中于一两部童话和描写自然生活的短篇故事,连《人参》、《叶芹草》这样的作品都难以受到青睐,更毋宁说那些始终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长篇和中篇小说。
面对现状,我们被一种深深的矛盾所支配。一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庆幸,许多成年人依然在不舍不弃地引导孩子阅读普里什文。我们不想否认这些经济行为背后的商业利益,但是在商业利润和对作家狭隘的理解之外,我们仍然能隐约感受到潜意识中的某种精神性存在:那就是对作家所深入思考的“自然与人”问题的关注和对亲近自然的民族文化传统得以薪火相传的冀望。然而另一方面,当普里什文仅仅是作为儿童作家被看待时,我们又感到无言的悲哀。悲哀来自我们对普里什文的些许理解:对他为人、为艺术的诚恳,对他一生所承受的压力和内心无以排解的矛盾,对他艺术中苦心追求的理解,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悲哀来自于他在今天俄罗斯读者中的不被理解,而且这样的不理解如果一成不变地重复下去,就会成为不断增生的误念,随着作品发行量的增大而流播得愈广愈深。只要将普里什文的专著与结集出版物的发行种类和数量稍加对比,就不难发现,普里什文作为“这一个”,作为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家的独特性正在无奈地消隐于“这一类”中。
可是早在20世纪初,高尔基就认识到普里什文作为艺术家的独特性。他夸赞普里什文的作品言之有物、结构严整、内容丰富、真实可感,达到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完美。他在《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中赞叹道:“在您的作品中,对大地的热爱和关于大地的知识结合得十分完美,这一点,我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都还未曾见过。”高尔基甚至将普里什文作为苏联文学的范本加以提倡:“通过他,我看到了似乎还不尽完善,却被一双天才之手描画的文学家的形象,苏联文学就应该是这样。”勃洛克在为普氏的特写集《在隐没之城墙边》所著的评论中也指出:普里什文极好地掌握了俄罗斯语言,许多纯粹的人民语言,虽然已经完全被当时“表面化的文学(主要指城市文学)所遗忘”,但对普里什文来说仍是鲜活、有力的。法捷耶夫则在致普里什文的信中承认:“《飞鸟不惊的地方》是培养我成人的书籍之一。”作为普里什文开创的哲理抒情散文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帕乌斯托夫斯基对这位文学前辈评价甚高。他认为,普里什文的一生是诚实的一生,他所写俱是其所愿,从不违心地趋时附势或追逐虚名小利。他这样的人永远都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人类精神的丰富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曾为不少名家高度评价的作家,今天却只被认定为写自然风景、民间故事和儿童文学的作家,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我们尤其想指出文学批评在此中所起的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由于受“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二元对立思维定势的影响,苏联批评界对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带有浓郁抒情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学一直采取漠视态度,将之视为肤浅的、缺乏社会教育功能的、远离人民生活的落后潮流。普里什文虽然称自己的创作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而且他一生中也写有大量的纪实性随笔,但其作品中占据相当分量的抒情和浪漫情绪在确立了他的“哲理抒情散文开创者”地位的同时,也使他长久地陷于边缘境地。
对以往研究中被忽略或研究不足的作家、作品的新的发现,体现的是一种“史”的眼光。从文学史建设的立场出发,重新研读普里什文不仅为了深入了解他以及他所发展的俄罗斯现代抒情哲理流派的艺术特质,同时对于把握其他流派作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观念,进而把握俄罗斯文学的整体也大有裨益。而且,作为中国的研究者,立足于当下的历史语境和中国人的阅读体验,普里什文对于我们未尝没有新的意义,未尝不会成为一种新的创造的历史资源而被继承和发展。普里什文所描写的自然美和人性美,因不合“阶级斗争”的时宜,在过去不仅不被重视,而且曾遭受粗暴的批判。今天看来,自然美和人性美这一创作母题对反思人性的丑陋残酷、净化人们的心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速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而且,普里什文是超前的,在一个以开发自然为基调的时代,他能够抵抗住种种诱惑和压力,把自己柔韧的美学触角潜入世界的原初和根本,这使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仿佛生活在时间之外或世界开端的诗人,他使自然成为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纳的文化;他试图恢复自然的本来面貌,从而使自然真正成为既诱使人去探究,却又永远无望穷尽的永恒;他使人由衷地感到对自然的需要,不仅因为那里有久违的纯净的阳光、水流和蓬勃生长的树木,更因为那里有越来越难以触摸到的人类的根脉,有一种别样的人生意境。他对于自然、大地的兴趣,近于一种纯粹的诗情,而其目标在于对人性的发现,对人生之为艺术的赏鉴。那一种对自然、对人生的品评赏鉴,以至赏鉴中的忘我,已难得见之于忙碌而粗心的现代人。我们痛感,这分明是我们某些能力的衰退或丧失,是我们正在流失的一种文化。也许有人认为普里什文简单,但是,他却能使自己并不繁杂的理论设想融于变幻无穷的自然现象,借助自然的无穷实现了艺术的丰富。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生的故事》中称:“普里什文仿佛就是俄罗斯大自然的一种现象”,“普里什文用两三行文字表达出来的这些观察结果,如果加以发挥,就足够另一个作家写出整整一本书来。”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上一篇:《金色的草地》课文图片
下一篇:《金色的草地》课文朗读
零零教育社区:论坛热帖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