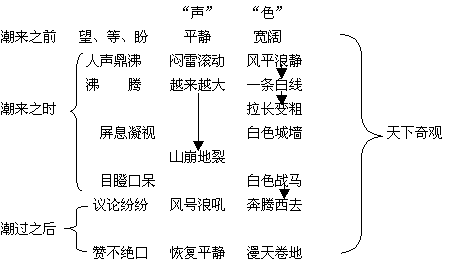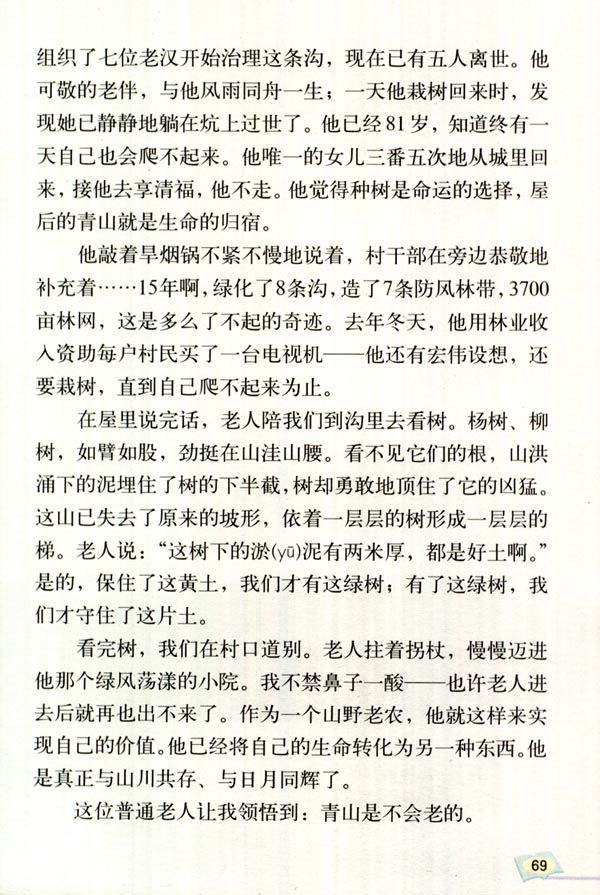《长相思》的精神三变——我的备课叙事
鲁教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丈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清]纳兰性德《长相思》
我上《长相思》,遭遇了一次奇妙的体验:上课的时候完成了备课的任务。这种完成,是自然的、下意识的,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去年7月的一天,正是毒日当头、酷热难耐的时候,李振村先生打了个电话过来,约请我在10月份举行的“全国首届中华经典诗文教学观摩研讨会”上作课。我口头是应承了,心里说,这不是“添热”吗?添热归添热,既然接了活,还是得把它做好。呵呵,我就这德性!
自从前年指导王自文上了《古诗两首》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去碰古诗教学了,伤神!那一课凌空出世后,一直像大山似的拦着我、压着我,让人心生“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诗是肯定不能碰了,那就碰碰词吧。其时,手头正好有本刚出炉的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的语文书。我就翻开来看,也是机缘巧合,一眼就看上了纳兰的《长相思》,连商量的余地也不留了。选公开课,第一感觉最是要紧。没感觉的课文,千万碰不得。
我捧起《长相思》,汗流满面地读了起来。本指望能读出点“人所未见、人所未发”之类的独门秘笈来,不曾想越读《长相思》反而越没了感觉。读到最后,原初的那种好感、那种迷离的冲动烟消云散,只剩下一层黏黏的汗垢留在身上。
怎么办?难道我与《长相思》只有一面之缘?换课!一念顿起;不能换!一念又起,我犹豫起来。末了,还是“不换”的念头占了上风。我对自己说,既然已经对《长相思》一见钟情,就不能再搞三心二意、见异思迁了。这样一想,心就定了。现在想来,这“心定”二字委实重要。《大学》开篇就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备课要有得,心定是关键。想想看,当初那心要是定不住,现在还轮得到你在这里为自己的《长相思》自说自话、自吹自擂吗?
尼采提出精神有三变:先变骆驼,再变狮子,最后成为婴儿。骆驼意味着接受训练,听从指导,传承前人的经验和文化。狮子则变得唯我独尊,自己作决定,对自己负责。婴儿象征着“完美的开始”,婴儿态让人的精神重新回到了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原点。《长相思》的备课历程,大体上就经过了类似的“精神三变”。
一
那个暑假,《长相思》一直黏在我的心头,成了我不能承受又不得不承受的生命之轻。心是定了,但对《长相思》的感觉还是处于没感觉的状态。必须换个读法,否则只会死路一条,我对自己这样说。于是,我撂下纳兰的《长相思》,转而去搜寻别人评鉴《长相思》的各种文字。是的,要想摆脱困境,我必须先成为骆驼,我也只能成为骆驼。感谢网络和藏书,让我在不到一天的工夫里,就积攒下1万多评鉴《长相思》的文字。这些文字在我眼前精灵般地摇曳,不但一波又一波地激荡起我对《长相思》的新的爱恋,也慷慨地为我提供了教学设计的种种灵感。
比如这一篇——
“山一程,水一程”,一种含而不露的循环句式,形成“行行复行行”的远离动作,动作的方向是榆关,与“故园”遥遥相对,随着行程的越来越远,造成空间上的巨大张力,产生对“故园”的依恋、渴望。“夜深千丈灯”,夜色深沉,千帐灯燃,然而这不是熟悉的家园的夜晚,怎能不惹起作者强烈的思归之情?“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作者多么希望能在梦中返回故园,但是帐外风雪交加的呼啸声使他难以入睡,这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辗转反侧的他怎能不埋怨这聒耳的风雪声呢?“故园无此声”,故园有什么声呢?是母亲的亲切嘱托,还是妻子的浅笑低语?引逗读者展开丰富的联想……
文字虽简约,意味却大有嚼头。我读《长相思》,就没能将“榆关”和“故园”搁在一块儿想,自然也就体会不到这种空间上的巨大张力。被他的文字这么一引逗,我顿时就听见了“行行复行行”这一句的沉重旋律:山一程,水一程——水一程,山一程——山一程,水一程——水一程,山一程……
又如这一篇——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翌年三月,玄烨出山海关至盛京告祭祖陵,纳兰性德扈从。本篇即作于此时。词以“山一程,水一程”六字叠韵发端,是此调正体,而全用口语组织,予人自然奔放之感,为下文“夜深千帐灯”五字拓开地步。此五字粗看亦寻常,细味之则朴素中兼有气象万千,为他人累千百字所刻画不到。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此深致推奖云:“‘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体味甚是,也足见纳兰此句之地位。下片作者情绪陡转。在“千帐灯”下,词人倾听着一更又一更的风雪之声,不禁想起“故园”,唤起“乡心”,从而辗转难寐了。此数句字面亦寻常,意思却很不一般。所谓“天涯行役苦”,大家都容易理解,可是纳兰现在乃是扈从皇帝“巡幸”途中,本该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才是。他却偏偏作此小儿女态,恋起家来!其深心视此等荣耀为何如即可想见矣。按其底里,真正是“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笔触之老辣,文字之古拙,让人爱不释眼。一句“其深心视此等荣耀为何如即可想见矣”,给人以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之感。而“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的喻指,可谓知根知底,深得容若文字三昧。纳兰在天有灵,必当以同怀视之。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和而不同、旨趣相左的鉴赏文字,比如这一篇——
“山一程,水一程”,仿佛是亲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是使命在身行色匆匆。“夜深千丈灯”则是大队人马夜晚宿营,众多帐篷的灯光在夜幕反衬下所独有的壮观场景。“山一程,水一程”,寄托的是亲人送行的依依惜别情;“身向榆关那畔行”,激荡的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萧萧豪迈情;“夜深千丈灯”催生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烈烈壮怀情。
这情感的三级跳,既反映出词人对故乡的深深依恋,也反映出他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出身豪门,风华正茂,自然是眼界开阔、见解非凡。又有皇帝贴身侍卫的优越地位,建功立业的壮志定会比别人更为强烈。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反而形成了他拘谨内向的性格,有话不能正说,只好借助于儿女情长的手法曲折隐晦地反映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
“夜深千丈灯”既是上阙感情酝酿的高潮,也是上、下阙之间的自然转换。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更何况“风一更,雪一更”,心情就大不相同。路途遥远,衷肠难诉,辗转反侧,卧不成眠。“聒碎乡心梦不成”的慧心妙语可谓水到渠成。
“山一程,水一程”与“风一更,雪一更”的两相映照,又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体验。愈是路途遥远、风雪交加,就愈需要亲人关爱之情的鼓舞。因为她是搏击人生风浪的力量源泉,有了她,为了她,就不怕千难万险,就一定会迎来团聚的那一天。从“夜深千丈灯”的壮美意境到“故园无此声”的委婉心地,既是词人亲身生活经历的生动再现,也是他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并以此创造美、抒发美的敏锐高超艺术智慧的自然流露。
说实话,以我偏爱的生命感觉和价值趣味,我更服膺第二篇的那种“不是人间富贵花”的心灵解读。而这种服膺,在我研读了纳兰性德的生平文字后,变得更为坚实。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康熙朝内阁大学士、太傅明珠的长子,顺治十一年(1655年)出生于满州正黄旗。纳兰性德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拜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为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又把搜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渌水亭杂识》,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纳兰性德22岁时,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授他三等侍卫,以后升为一等侍卫。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纳兰性德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儒雅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著称于世。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后更名为《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2首,编辑一处,名为《纳兰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纳兰性德十七岁时娶妻卢氏。少年夫妻无限恩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词创作。卢氏于婚后三年因难产去世。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关氏,并有侧室颜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暮春,纳兰性德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一岁。
一方面是落拓无羁的性格,天生超逸的秉赋,卓尔不群的才华,一方面又是钟鸣鼎食的富贵,平步宦海的潇洒,金阶玉堂的桎梏,这构成了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心理压抑和人格裂变。加之爱妻早亡,后续不洽,知交零落,扈从艰险,使纳兰性德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其深心视此等荣耀为何如即可想见矣!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上一篇: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和解”
下一篇:《长相思》教学反思之一
零零教育社区:论坛热帖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