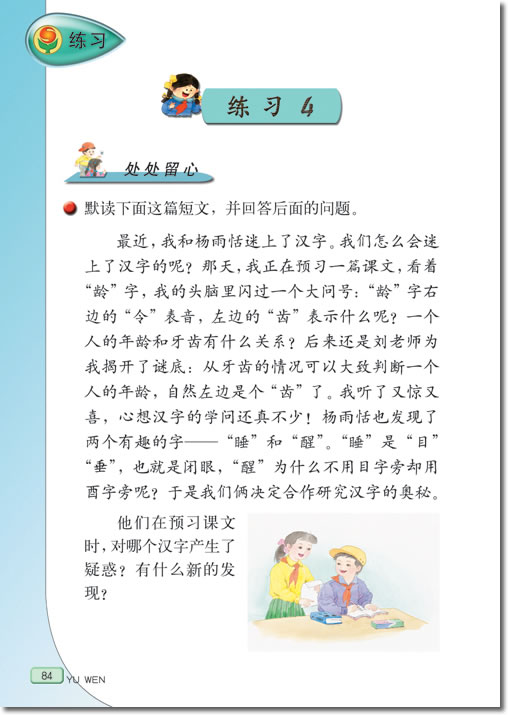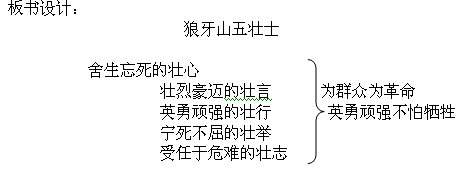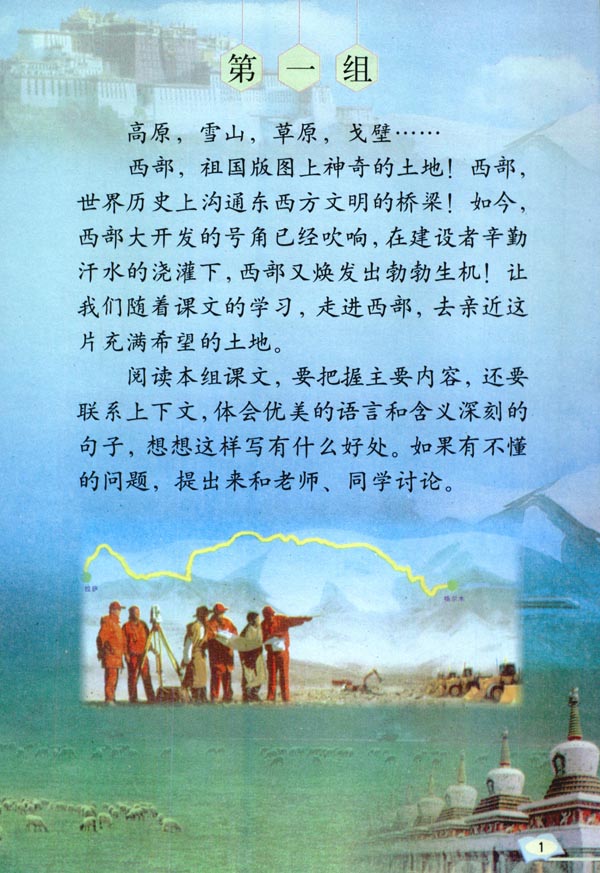百年祖堂
湘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就像所有聚族而居的村子一样,村里有个祖堂,一个祖辈魂灵打盹儿的地方。
祖堂不知哪代人所建,自北而南竖在山村中央。那是全村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最长的建筑。祖堂一进三重,地面逐重升高。三重之间,天上由长长的天井隔断,地下则由宽宽的石级相连,石级顶处是两条贯通东西的村巷。这种似断实连的结构,比那种三重外墙相连的祖堂好,一是方便了村人行路,二是融入了生活气息。
地势最高的上祖堂,平日大门一般锁着,也许是怕小孩到那儿玩闹惊扰了祖先的宁静,其实,立着祖人牌的屋子,阴森森的,空气中仿佛有种异样的东西存在,孩童一般是不轻易进去的。祖堂后墙有一砖砌高台,五六块形同墓碑的木牌在上面摆着,就是远远站在门口,对它们也只能仰视。牌位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历代逝者的名字,由于位置太高,谁也看不清楚,也没有谁想看清楚。在我等后辈人心目中,它们只不过是对祖辈表示敬意的一个符号。乡里人如果遇到什么祸事、险事,结果无大碍,人们就会说他“祖人牌位坐得高”,那是一句恭维话,意思是祖先护佑着他了,能够遇难呈祥。说的人不当真,听的人也不会当真。
牌位往前是香案、香炉和磬,右侧墙上嵌一面画着八卦图案的牛皮鼓。前有古,后有例,清明、七月半、春节前后,家家大人带了小孩到这里供饭,烧香,磕头,作揖。叫祖人吃饭要敲磬,祖辈们的魂灵在打盹儿,敲几声就把他们敲醒了,醒了才能象征性地享受子孙奉献的米饭佳肴,领受子孙的孝心和敬意。那面鼓好像不能随便敲的,村里的后生接了新娘子到这里行大礼时才能用,似乎只能用这种宏大的声音,才能传达出后辈人的感恩和惊喜。在昔时,若村里没有红喜事,上祖堂的鼓声突然响起,就不是什么好事了,那是“整家规”的信号。清末某年,族长在上祖堂把鼓一擂,全村人闻声赶去。只见地上铺着狗儿刺,不一会儿,一个与外村人有苟且的童养媳被推搡进门。她被剥光衣服,只穿一件裤衩,被迫滚狗儿刺,滚得鲜血直流。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祖人似乎不那么重要了,闹房头,闹宗派,是要受到官方谴责的。这时,上祖堂做了生产队的仓库。曾经神圣的牌位前,靠墙一溜儿挤着大大小小的甏,甏里装着各类种籽;昔日人们跪拜之处,立着篾围子围成粮囤,囤着待分的社员口粮;粮囤间的空地也堆着谷物,甏里、囤中、堆上,盖满白色的灰印。冥冥中的祖人充当了后人“口中食”的守护者。过了几年,破四旧风起。祖堂的牌位被一把火烧光,香案、香炉、皮鼓等一应物什都扫地出门。村里建了新仓库后,这里成了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除了晚上偶尔开会,没有人来。七十年代中期,一家井巷公司子弟小学还未建起,三重祖堂都成了临时教室。几十年间,上祖堂那些曾在打盹的祖先够可怜的,受到空前的冷落。
应了中国一句老话,风水轮流转,《国际歌》唱了近半个世纪后,不知一阵什么风把曾经消失的一切又吹了回来,修宗谱,接太祖,唱太公戏,都成了乡下人十分热衷的事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上祖堂又恢复了原来的效用,祖宗牌位重立,香案、香炉、石磬、皮鼓等一切各归原位,每年清明、七月半,特别是除夕到年初,内面香烟缭绕,红烛高烧。偶尔回乡,我也免不了去那儿,免不了焚香跪拜,不过是入乡随俗,并不很情愿的。我想,敬祖人在心,而不在仪式。
中祖堂和下祖堂,除了建筑上的联系之外,它们与那些打盹的魂灵没有多少瓜葛。
前后无隔墙的中祖堂,像一个很宽的胡同,除了在梁上吊几架水车之外,两壁皆空。在上辈人的记忆中,中祖堂是个令人快活的去处,这里白昼晚间都满是人。住在祖堂左侧的海哥,家道殷实,不靠他下地干活。他读过很多说部、古传,又性喜吹腾。于是,白天,一班毛头小伢围着海哥,听他谈文,谈三国,谈水浒,谈西游,谈岳飞传,谈济公传。海哥门槛上坐着的油灯,预示了村人夜生活的开始,老头、爷们捏着老竹头烟杆来了,妇女、老太把纺车也搬来了,坐不下的,挤到了村巷上。人一多,海哥谈兴更高,在咝咝的吸烟声和嗡嗡的纺线声中,绰号“海喇叭”的海哥,亮起嗓门吹着他神奇的“喇叭”。那是山村多么美好的夜晚!
很遗憾,海哥给村里人带来的精神盛宴,我无缘享受,等我出世已见不到海哥了,但中祖堂还是一个充满活气的地方。每隔半月,邻村的剃头匠就在这里操“顶上功夫”,给村里的男丁剃光头、东洋头、锅铲头。剃头匠是个练武的,手劲特别大,他左手拇指、食指、中指,铁钳一般钳住人的头,钳得人头皮又麻又疼。剃头间歇,他喜欢炫耀自己的功夫,有人拿来一把锄头,横在他和三个壮汉之间,他右掌抵住的锄柄,把壮汉们推得直往后趔趄。在修理农具的季节,生产队请来的木匠,在这里忙乎乎地摆弄他的墨斗、锯子、斧锉。木匠刨新木时,一串串刨花由刨口奔窜而出,那一声声亮响分外好听。做小孩时,常捡那些纤薄而卷曲的刨花回家,母亲放进瓷皿用水浸了抹头发。阴雨天,这里堆满了稻草,大爷、叔伯从各家提了矮凳子、揣了要桩子,来这儿打草要,一个个结实的草要就像五六寸高的钢筋弹簧似的。年底,或许哪家要嫁姑娘了,邀了个弹棉絮的来,弹絮的背着一张木弓,坐在一条矮而长的条凳上,一手扶弓,一手舞棰,“穹穹穹”的声音与花绒毛屑一同飞舞,在孩童耳中那是极动听的音乐。
一年中偶有一两次,中祖堂氤氲着悲哀气氛。中间停放着亡人入殓后的棺材,棺下点着称为“落气灯”的菜油灯盏,棺前挂着宽宽的粘着挽联的孝帐,孝帐前是搁着牌位和祭品的矮桌。村里只要能抬腿的都来彻夜守灵,一个个哀哀戚戚。不过,这样的日子毕竟短暂,哗啦啦的生活流水经过短暂的阻断后,继续欢实地在这里流淌。
下祖堂地势最低,它北面无墙,梁上堆放着干苕藤和牛草,靠东北角有一个石碓。在没有电动轧米机的年代,这里是全村的粮食加工地,家家户户轮番在这里舂米。小时候常跟母亲一起去舂碓,拿棍子拨拉臼中的谷物,间或与母亲一起踩碓,母亲总是夸说道:好,一个鸡公儿四两力!年底舂糯米粉、高粱粉,是下祖堂最忙碌的日子,这家舂完了那家来,入夜好久了,舂碓的钝响还叩击着全村人的耳鼓。住在下祖堂左侧的秀娘,从来没有为此嘟囔过,这孤零零的老人怕的就是寂寞。每当谁家来舂碓,她都要掇把矮竹椅来,与舂碓的主妇拉话。秀娘牙齿掉光了,说话口齿不清,又颠三倒四的,孩童听了笑断肚肠。
这里有时成为“女人国”,男劳力在中祖堂打草要的日子,姑娘、婆姨们往往被派到下祖堂搓草绳。绞辫子绞惯的手,搓绳子还不是拿手好戏?这样的阵势,男女之间打口水仗的事情是自然要发生的,那些自诩“油嘴不油身”的人,唾沫星子里往往含着色情的气息。在草窝钻进钻出、翻筋斗的孩童啥也不懂,而那些刚有了心事的小女子们,一张张脸往往臊得如血泼一般……
由于社会变迁,中祖堂再也听不到谈笑声、刨木声、弹花声,见不到剃头匠耍武艺、男子汉打草要的身影了,同样,下祖堂也听不到舂碓声、唠叨声、骂俏声,见不到两腮染上霞色的村姑、头上粘满草屑的孩童了。两重祖堂就像锅底撤了火的蒸笼,再没有一丝生活的热气在这里蒸腾。近年经过几次整修,三重山墙已连为大一统的整体,唯一的出口老是挂着门锁,这两重祖堂与上祖堂一样,只拥有坟墓一般的死寂。它们葬埋了往事,葬埋着空气,晴天或雨天,只有瓦缝透过的光缕,或破瓦漏下的水滴,是这偌大死寂空间里唯一活动的东西。
对已然回归纯粹祭祀意义的祖堂,我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就像对乡野上的土地庙那样。去年雪天,回了趟老家,发现祖堂又粉刷一新,村人都在为迎接太祖驾临而忙碌,其中还有向镰刀斧头旗帜宣过誓的人。这样折腾,令我感到几许悲哀。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上一篇:《一棵大树》教学设计之一
下一篇:与爱同行 不忘感恩
零零教育社区:论坛热帖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