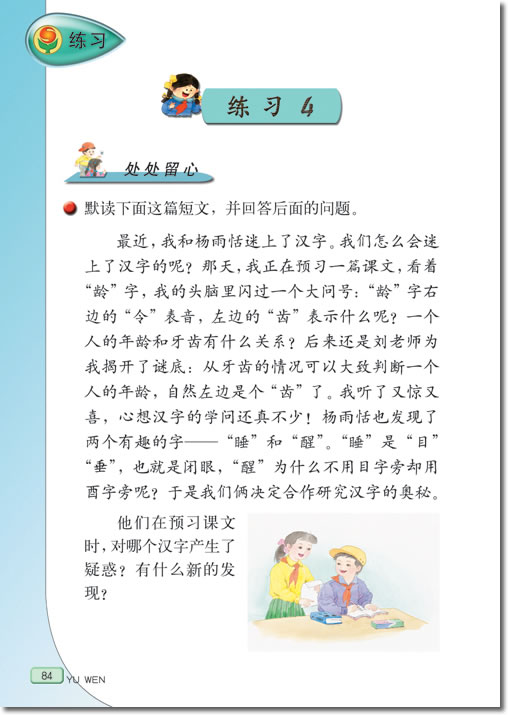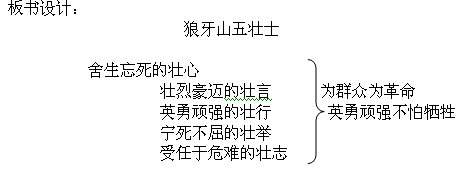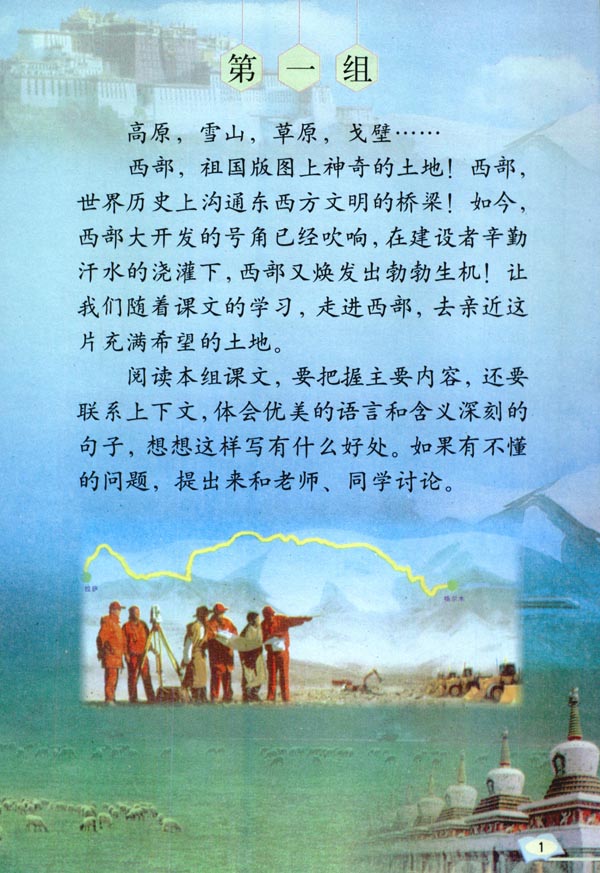东爿西爿
湘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整个山村的建筑格局,以祖堂为中轴线分为东西两爿,平面仿佛一只伏地的粉蝶。
西爿屋宇多是村里年代最久的房子,屋瓦连成一片,硬是有“谁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情谊。因了这样的“情谊”,西爿有了一纵两横三条干巷。从中祖堂前过来的那条巷子最黑,清晨、傍晚当面看不见人。它的西尽头是一小块空场,上覆屋瓦,人称“过棚”。由于三面通风,“过棚”是村里伏天的消暑胜地。那儿有不少石墩,在西禾场打场的人、挑水粪上放牛场的人喜欢在这里歇凉,大人小孩每每把午饭端到这里吃,吃完就在石墩上坐着打盹。
“过棚”西边是川伯家新屋。那是村里顶规整的房子,前墙青砖到顶,青石门框门槛,堂屋高朗敞亮,厢房深阔气派,让人想到“画”、“堂”等左右对称的汉字。这家人方方正正,像他们的房子。有一年汉奸来村里抓人,川伯被抓进李客冲,汉奸要他供出村里的地下党,川伯任他们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怎么也不开口。待汉奸折磨够了放人,四十出头的川伯成了瘸腿走路、白发满头的老翁。川伯的长子雾哥是心地纯正、行事端方的读书人。我读大学时,妻子在企业做饭,每每要忙到夜分,在企业做会计的雾哥受我之托尽心关照。每天晚上,妻子苦留他吃点“不吃白不吃”的饭,雾哥从来不肯占便宜,总是回村吃过饭后,再摸一里多黑路,去那里接她回家。这个好人前年去世了,可惜我没得信未能回去送他。
“过棚”之东,一连好几家。靠北是孙娘家,一重连三的土坯房坐北朝南,与后祖堂边几间空空的土房连成一排。孙娘家后院是一片竹林,其居可算村里的“潇湘馆”。“潇湘馆”隔一干巷往南是风哥家。他家房子有点不正,外墙是一巨大的扇形,屋里迷宫一样,堂屋深藏其内,左右厢房数间黑古隆冬的,整座房子很像一个远古的城堡。“城堡”没有正门,在向西的披厦上开了个后门,出门就是“过棚”。
与“城堡”隔着那条著名“黑巷”,往南是茗哥家。茗哥家房子如摊开的古帖,成一长条铺向村子最南端,夹在众多厢房中的堂屋,既无朝门洞,也没有大门,向西开了个后门。这幢房除东向没门窗外,其余三向均有,因此屋子还算亮堂。如帖书的房子,蕴一脉书香。茗哥的父亲卿先生是一方名儒,在堂屋课徒授业,教人念《诗经》、《易经》。乡人敬称他“红笔师爷”,砚田功夫很是了得。村里的女人很怕他,路遇女人趿鞋、蓬头,他都劈头盖脑一顿训斥。据说,有天他拄着文明棍,踱到张家大湾,见塘边灌木上晾着不少女人衣裤,他勃然大怒,用文明棍把这些不雅的布片悉数挑进水中,边挑边嚷:“成……成什么样子!成……成什么样子!”老先生有点口吃。茗哥家读书种子连绵不绝,村里二十多名大学生,他一家占了六个,孙儿、孙媳都留学美国。
中祖堂西是海哥家,海哥家宽大的堂屋紧贴南干巷,往北是一长溜愈来愈浅的厢房,直到北干巷。这房屋像煞一只巨型“海螺”。巷南落地三尺是飞伯家的半边连二,西边是堂屋,北有披厦,东有厢房,半包着堂屋,像个左、下各缺一笔的“回”字。它夹在茗哥家和下祖屋之间,像一庞大的动物被羁勒着,而这片屋瓦下的人却不是孬种。飞伯三年自然灾害时当过村官,上面开会说要来村里估查存粮数,他得知信息后号令全村老少上阵,一夜把四个玉米堆剥个精光,只剩下可怜兮兮的两个玉米堆让人过目。大饥荒那几年,村里没有饿死一个人,多亏了飞伯瞒下的几千斤玉米粒。飞伯的儿子靖哥爱打抱不平。那年,一伙蕲春造反派为争待遇,要把姓汪的矿长揪到蕲春去。那伙人不时捡起铁道上的石块砸,矿长汗衫被撕破、身上流着血。靖哥刚好出工路过,带领伙伴们一拥而上,要那伙人放手。造反派仗着人多势众,继续推搡着矿长往前走,靖哥把邻村地上干活的都吆喝了来,蕲春人见架势不好才纷纷逃散。可叹一身侠气的靖哥,后来殉情自尽了。
东爿村屋不像西爿一样屋瓦颠连,从北到南分成三个层次。
最北的房子是鲲伯和他两个儿子的,从上祖堂门口穿过北干巷,就到了他们家。那一重连五的房子,深陷于几丈高的陡坡下。房子怪怪的,堂屋没法开大门,被人家山墙堵死了,只好开在南厢房前。窗户怪怪的,全是竖条形,外面狭小,拳头都伸不进来,内面稍宽,窗框成八字展开。鲲伯却一点不怪,是个非常正派厚道的老人。他懂点医道,村里有人得了疑难杂症,总是去问他。鲲伯热心快肠替人解忧,但从不图人一丝回报。他说:半文钱不落虚空,我怕还来生债!鲲伯没活干的时候,喜欢在他家东面的梨园墙根躺着,静静地晒太阳,老人八十多岁无疾而终,姜娘三天之后也赶到另一世界去陪他。
鲲伯家往南,三排西向房子横列着。六娘家的房子与鲲伯家南厢房隔条巷子,结构与孙娘家一样,门头上画了个八卦,八卦下吊面镜子,给人一种莫名的神秘感。屋前出檐有一米多宽,檐下那条直通鲲伯家门口的土路,永远是干爽的。六娘早寡,含辛茹苦养大独子雪哥。她勤苦持家在村里算得第一,一个鸡腿或是一块肉,客人走了又放进坛里腌着,前前后后起码要放三年。六娘喜欢的是小孩,谁家媳妇要生产,她都紧迈小脚赶去接生,村里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是由她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是,我女儿也是。这样一位好心肠的老人,却非常不幸。雪哥不到三十患了急性黄疸肝炎,年轻的生命像雪一样融掉,留下白发皤然的六娘。
往东隔一宽沟,是川伯家一重连三的旧宅,南面是别家几间小房。再往东隔着空基是我祖父的房子,也是一重连三,南墙边是灯家一隔为三的长房。祖父母勤俭兴家,在一方也颇有口碑。他上街下县连草鞋也舍不得穿一双,连烧饼也舍不得买一个吃。村里人和他一道到县衙还钱粮,没有谁愿意他去置办伙食的,若是他办,主打的是白菜、萝卜、藕带,荤菜也只是几十条寸把长的小鱼,能把大伙的嘴淡出鸟来。祖父母的俭省常人难以理解,就是接了新谷,他们还是吃糠粑当饭,客人来了藏都藏不赢。一块肉老是在豆酱里蒸着,吃饭时箝着抹一下嘴唇,对人说“吃过肉了”。祖父母没等我这晚孙向他们报到,就走向了不可知的世界。等我面对这所老宅时,主人已是笑眯眯的大伯了。
上面那三排房子的山墙出檐都很宽,檐下干路与六娘屋前的干路垂直相接。干路往南是下段,三家房子一字儿摆开。四伯家朝西,锴叔家朝南,我家则朝东。四伯堂屋靠北,厢房在南,像个“田”字缺了中间一竖的上半(我家则恰恰相反)。堂屋背后,是一条上面盖瓦、南北有门的公巷。隔着公巷就是锴叔家,他的半边连二,与飞伯家一个模样,为人性气也相似。1968年,县里召开万人大会,会间他去医院探望本村腿骨生了怪病的灯。得知灯动手术抢救需要足够的血浆,锴叔哽也不打就说:抽我的!锴叔300CC鲜血,把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七八年前,母亲重病过一次,我和弟弟在外毫不知情。邹婶从窗户中看见她咯血满床、昏迷不醒,就掇梯翻院墙进屋料理照顾,把血污的衣被洗得干干净净。她把“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语,续写为“远子不如近邻”。
以上是我离乡之前山村人家的大致模样。那些拥挤的土坯房,尽管简陋而不规则,但充满活气,充满柴米油盐气息。最让人怀念的是像脉络一样贯通全村的干巷和干路,那些雨雪难侵的路,使村人随时都可以安然串门,心与心因此贴得更近。我祖母与茗哥母亲的夜谈之雅,是老辈人津津乐道的。她们俩都是饱读诗书的人,出声透气都带着书香。两位小脚的老人,一聊就聊到深夜,分手总是你送来我送去,在“之”字形的干巷、干路上,不知要往复多少回……
如今,山村大变样了。原来的建筑格局不可复寻,单门独院的钢筋水泥楼房,已成为村屋的主体,它们使村庄变得臃肿不堪,原来的小“粉蝶”变成了特大“阴阳蓝凤蝶”。所有的干巷、干路,都已消失在疯狂的扩建中,雨天、夜分随意串门已成往事。也没多少能串门的人了,不少楼房是“空心”的!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零零教育社区:论坛热帖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