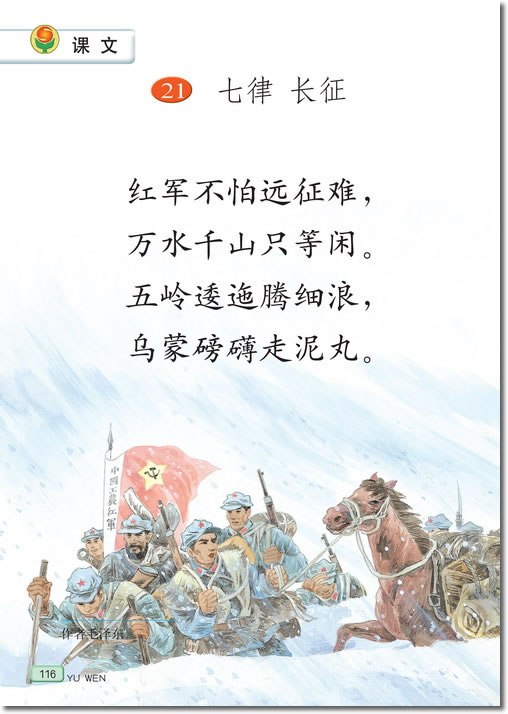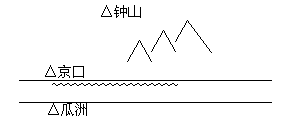单元教学
听雨季羡林
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
“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文字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
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章用回忆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添秀句,每闻夜雨忆联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它一下: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五十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童山濯濯”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
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六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决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蒙蒙。
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
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画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逝方生,方生方逝。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
我的心又收近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怡悦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1995年4月13日)
第三课 《草虫的村落》
一、作家档案
郭枫 著名诗人、作家。读高中的时候,郭枫在《宝岛文艺》发表长篇叙事诗《北方》,即受文坛瞩目。1950年起,郭枫成为《半月文艺》《中国文艺》《大公报》《时代青年》《野风》《宝岛》等刊物的主要撰稿人。1988年开始,郭枫为了在台湾振兴中国文学而奔忙,他还在北京大学设立“郭枫文学奖”。他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早春花束》《九月的眸光》《老家的树》《永恒的岛》;诗集《郭枫诗选》《第一次信仰》《海之歌》;论文集《高举民族文学的大旗》等。
郭枫是一位民族意识和传统意识强烈的作家,他常常通过对黄淮平原的回忆,表现他对故乡的真挚热爱之情。从上世纪50年代的《黄河的怀念》到60年代的《山》,再到80年代的《我想念你,北方》,都表现了他对古老的中华大地的深情怀念。他写的《老家的树》,以饱满的激情,用柳树的妖媚、榆树的粗犷、白杨的潇洒、松柏的高洁象征北方的人民,象征中华民族的深沉、高洁、苦难与奋进,从而创造出情融于景、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
二、名家走笔
昆虫的故事孙犁
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成年以后的欢乐,则常带有种种限制。例如说:寻欢取乐;强作欢笑;甚至以苦为乐等等。
而童年的欢乐,又在于黄昏。这是因为:一天劳作之后,晚饭未熟之前,孩子们是可以偷一些空闲,尽情玩一会儿的。
时间虽短,其欢乐的程度,是大大超过青年人的人约黄昏后的情景的。
黄昏的欢乐,又多在春天和夏天,又常常和昆虫有关。
一是捉黑老婆虫。
这种昆虫,黑色,有硬壳,但下面又有软翅。当村边的柳树初发芽时,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群集在柳枝上。儿童们用脚一踢树干,它们就纷纷落地装死。儿童们争先恐后地把它们装入瓶子,拿回家去喂鸡。我们的童年,即使是游戏,也常常和衣食紧密相连。
二是摸爬爬儿。
爬爬儿是蝉的幼虫,黄昏时从地里钻出来,爬到附近的树上,或是篱笆上。第二天清晨,脱去一层黄色的皮,就变成了蝉。
摸蝉的幼虫,有两种方式。一是摸洞,每到黄昏,到场边树下去转游,看到有新挖开的小洞,用手指往里一探,幼虫的前爪,就会钩住你的手指,随即带了出来。这种洞是有特点的,口很小,呈不规则圆形,边缘很薄。我幼年时,是察看这种洞的能手,几乎百无一失。另一种方式是摸树。这时天渐渐黑了,幼虫已经爬到树上,但还停留在树的下部,用手从树的周围去摸。这种方式,有点碰运气,弄不好,还会碰到别的虫子,例如蝎子,那就很倒霉了。而且这时母亲也就要喊我们回家吃饭了。
捉了蝉的幼虫,回家用盐水泡起来,可以煎着吃。
三是抄老道儿。
我们那里,沙地很多,都是白沙,一望无垠,洁白如雪,人们就种上柳子。柳子地,是我童年的一大乐园。玩累了,坐在沙地上,就会看见有很多小酒盅似的坑儿。里面光滑整洁,无声无息,偶尔有一个蚂蚁或是小飞虫,滑落到里面,很快就没有踪迹了。我们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道儿,老道儿,我给你送肉吃来了。”一边用手往沙地深处猛一抄,小酒盅就到了手掌,沙土从指缝里流落,最后剩一条灰色软体的,形似书鱼而略大的小爬虫在掌心。这种虫子就叫老道儿。它总是倒着走,把它放在沙地上,它迅速地倒退着,不久就又形成一个窝,它也不见了。
它的头部,有两只很硬的钳子。别的小昆虫一掉进它的陷阱,被它拉进土里吃掉,这就叫无声的死亡,或者叫莫名其妙的死亡。
现在想来:道家以清静无为、玄虚冲淡为教旨。导引吐纳、餐风饮露以延年。虫之所为,甚不类矣。何以千古相传,赐此嘉名?岂农民对诡秘之行,有所讽喻乎?
三、名人自传
爱好昆虫的孩子——法布尔
现在,有许多人总喜欢把一切人的品格、才能、爱好等归于遗传。也就是说承认人类及一切动物的智慧都是从祖先那儿得来的。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我现在就用我自己的故事来证明我那喜爱昆虫的嗜好并不是从哪个先辈身上继承下来的。
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从来没有对昆虫产生过丝毫的兴趣和好感。关于我的外祖父,我不大知道,我只知道他曾经历过相当苦难的日子。我敢说,如果要说他曾经和昆虫发生过关系的话,那就是他曾一脚把它踩死。外祖母是不识字的文盲,每天为琐碎的家务所累,没有什么闲情雅致去欣赏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对于科学或昆虫当然更不会产生兴趣。当她蹲在水龙头下洗菜的时候,偶尔会发现菜叶上有一条毛虫,她会立刻把这又讨厌又可恶的东西打掉。
关于我的祖父母,我知道的比较详细。因为我小时候,我的父母穷得无法养活我,所以在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跟着祖父母一同生活了。祖父母的家在偏僻的乡村里,他们靠着几亩薄田维持生计。他们不识字,一生中从没有摸过课本。祖父对于牛和羊知道得很多,可是除此之外,其它的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如果他知道在将来他家里的一个人花费了许多时间去研究那些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昆虫,他会多么地吃惊啊!如果他再知道那个疯狂的人正是坐在他旁边的小孙子,他将一定会愤怒地给我一巴掌的。
“哼,把时间和力气花费在这种没出息的东西上!”他一定会怒吼。
祖母是一个可爱的人,她整天忙着洗衣服,照顾孩子、烧饭、纺纱、看小鸭、做乳酪和奶油,以及其它一些家务,一心为这个家操劳。
有时候,在晚上,当我们都坐在火炉边的时候,她就会常常讲一些狼的故事给我们听。我很想见一见这匹狼,这位在一切故事里使人心惊肉跳的英雄,可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次。亲爱的祖母,我是始终深深地感激着您的。在您的膝上,我第一次得到了温柔的安慰,使痛苦和忧伤得到缓解。你遗传给了我强壮的体质和爱好工作的品格,可是你的确没有给我爱好昆虫的天性。
我自己的父母都是不爱好昆虫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父亲小时候虽然进过学校,稍稍能读能写,可是为了生活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再也没有时间顾及到别的事情了,更谈不上爱好昆虫了。有一次当他看到我把一只虫子钉在软木上的时候,他狠狠地打了我一拳,这就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鼓励。
尽管如此,从幼年的时候开始,我就喜欢观察和怀疑一切事物。每次忆起童年,我总会想起一件难忘的往事,现在说起来还觉得很有趣。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光着脚丫子站在我们的田地前面的荒地上,粗糙的石子刺痛了我。我记得我有一块用绳子系在腰间的手帕——很惭愧,我那时常常遗失手帕,然后用袖子代替它,所以不得不把宝贵的手帕系在腰上。
我把脸转向太阳,那眩目的光辉使我心醉。这种光辉对我的吸引力相当于光对于任何一只蛾子的吸引力甚至还要大得多,当我这样站着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突然冒出一个问题:我究竟在用哪个器官来欣赏这灿烂的光辉?是嘴巴?还是眼睛?请读者千万不要见笑,这的确算得上一种科学的怀疑。我把嘴也张得大大的,又把眼睛闭起来,光明消失了;我张开眼睛闭上嘴巴:光明又出现了。这样反复试验了几次,结果都是一样。于是我的问题被我自己解决了:我确定我看太阳用的是眼睛,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叫“演绎法”。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现啊!晚上我兴奋地把这件事告诉大家。对于我这种幼稚和天真,只有祖母慈祥地微笑着,其余的人都大笑不止。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