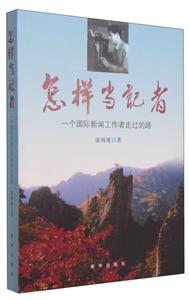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

|
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叙旧文丛作者:肖伊绯 著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5334-6925-2 定价:39.00元 出版时间:2015-09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
而另一幅新近公布出来的周作人自寿诗手迹,则是周于1960年题赠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据周1960年10月13日致鲍耀明信,则可约略知道1960年这幅题诗的来龙去脉。信中提及:“命写旧诗,兹以曲园旧笺(系曲园后人用旧版新印者,亦已廿年前的事了)写一通,聊以塞责,只有墨而无宝也。该笺疑用的是洋红(?),恐不能付袜,裱了怕沁。”
这幅题诗的确很特别,没有上款,没有“自寿诗”之谓,也没有后来改题的“打油诗”之称,确实也没有装裱,哪怕是简单的托裱也没有,只是两张原样的薄薄笺纸。题诗的笺纸确也特别,为红格信笺,笺右侧上方印有“仿苍颉篇六十字为一章”,左侧下方印有“曲园制”字样。这种笺纸,其实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号曲园)所制;而之所以在民国时代还能用到这种“前清遗制”,则有赖于周作人的学生、俞樾曾孙俞平伯(1900-1990)的重印。
1930年6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俞平伯所著《燕知草》,其中就附印了这种笺纸。俞还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出卖信纸”的小文章,其中提到,“我有一种旧版新印的信笺,大家一商量,大可出卖,而且莫妙于沿街兜卖。其时正当十一年四五月间”。可见,这种俞氏家族“旧版新印”的笺纸,最早在民国十一年(1922)就面世了;而俞本人手头存有一些,并将之赠予其师也是人之常情。20余年后,周应香港新朋友之请,拿这特别的笺纸来写当年的“自寿诗”,自是别样风味罢。只是从笺纸的行格布局来看,一首自寿诗写完刚好合适,别无空处题写赠言之类;再以美观角度而言,着实再也写不下多余的行款、题款、落款来了。但就书法的精深醇熟而言,时年75岁的周来写当年的五十自寿诗,的确已臻至化境,老笔成精矣。
◎1944:出任伪职再打油
以上这八幅自寿诗一一看毕,似乎仍意犹未尽,按常理推测,周作人应该还会有自寿诗的再续之作罢。其实,当周60岁寿期临近之际,无论是他的故友新朋之间,还是普通读者之中,也都在揣测与议论,看是否又有所谓“六十自寿诗”之类的新作问世。
1944年9月,周作人果然又辑录了24首打油诗来发表。发表时特别声明,这次辑录的打油诗与六十自寿无关;而且先前的五十自寿诗,也是林语堂“硬说”的,原本也只是打油诗而已。在这份特别声明中,周氏竭力说明了不再写自寿诗的原因,归结起来,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那两首诗发表之后,在南方引起了不少的是非口舌,闹嚷嚷的一阵,不久也就过去了,似乎没甚妨害,但是拨草寻蛇,自取烦恼,本已多事,况且众口烁金,无实的毁谤看似无关重要,世间有些重大的事件往往可由此发生,不是可以轻看的事情。鄙人年岁徒增,修养不足,无菩萨投身饲狼之决心,日在戒惧,犹恐难免窥伺,更何敢妄作文诗,自蹈覆辙,此其一。”二是“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谓僧腊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在家时期的一部分抛去不计,假如在二十一岁时出家,到了五十岁则称曰僧腊三十。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从那一年即民国二十八年算起,到现在才有六年,若是六十岁,那岂不是该是民国八十八年么。六十自寿诗如要做的话,也就应该等到那时候才对,现在还早得很呢,此其二。”
如果说第一条理由尚可理解为,那是一位闲逸之士不愿招惹事非,但求耳根清静的尘外之想;那么,第二条理由则颇令人不解,原来这位一直活跃在沦陷区文化圈子里的人物竟然出家做和尚了?而且出家为僧的时间,恰恰在他五十五岁之后,即1939年之后,这又做何解释?
返观史料与史实,周作人自认的所谓“僧腊”之始,却正是其投日事伪、锋头正劲之时。此时,他已经先后出任日系势力控制的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伪北京大学筹备员、伪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理事、评议员等一系列伪职了。在其“僧腊”的第二年,也即1940年12月1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还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从此,他有了正式的汪伪政权行政职位,成为行政“长官”,而不再仅仅是担任由日伪势力管控的各类文教、社团类职务。
此后,周作人又出任新民总会委员、伪华北综合研究所副所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北京图书馆馆长、《华北新报》理事及报导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安清道义总会顾问等伪职。如此看来,实可谓左右逢源、风光无限,其文化影响力在沦陷区正逐渐“壮大”起来,而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什么闭门谢客、“出家为僧”之状。
还有一些善于揣摩“微言大义”的研究者,声称周作人所谓的“僧腊”计算方法,是暗示“出家”即为“出山”之意。这种观点认为,在北平沦陷期间,周作人等遗留在此的文人群体皆自命为“遗民”,有某种清初明末的“遗民”情怀。在这个“遗民”圈子里,他们心照不宣的默认,“闭门谢客”者即如同明末“逃禅”的狂士山人,“出门做事”者即如同明末出山迎奉清廷的“新民”。换句话说,周作人认为只要不再“闭门读书”,走出家门,即是“出家”;他投日事伪之时,即为“僧腊”之始。当然,他或可称自己有某种“家累”之苦衷,还有某种“道义事功化”之信条,只能“出家”去追求事功。不管怎么说,周作人的“出家”,就是“出门做事”的意思罢。
无论这种文化想象式的揣摩,是否理据充分,但也总算是把“出家”与“僧腊”的关系,联系了起来。曾以明末遗民自命也罢,再以事功“新民”自许也罢,周作人终于“出家”,已成定局。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一点,周作人的“出家”,与“出家为僧”不是一回事儿。那么,他刻意提出“僧腊”一说,来含糊其辞,来故布疑阵,这其中又有何奥妙呢?
社科图书 人文历史
在线阅读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