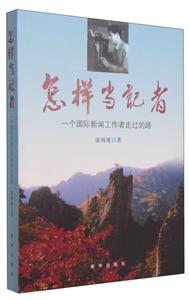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作者:让·埃默里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545914573 定价:42.0 出版时间:2018-05-01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
我想要谈论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或者按以前的叫法,那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den geistigenMenschen),首先就必须对我的对象,也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加以定义。按照我所使用的含义,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肯定不是每一个进行所谓脑力劳动的从业者。正规的高等教育也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律师、工程师、医生,很可能还有语文学家,他们虽然聪明,甚至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非常杰出,但鲜有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一个知识分子,如我理解的,是一个在广义上的精神脉络里生活的人,与其相联系的是一个本质上人本的或者说人文学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审美意识,秉性和能力驱使他进行抽象思考。思想史上的一系列景象在每一个合适的时机都会在他脑海中浮现。如果有人问他,哪个名人的名字以“ Lilien”开头,他想到的不会是滑翔机设计者奥托·冯·利林塔尔(Otto von Lilienthal),而是诗人德特勒夫·冯·利里恩克龙(Detlev von Liliencron)。给他一个关键词“ Gesellschaft”,他理解的不是世故、善社交,而是社会学。引起短路的物理过程他没有兴趣,对宫廷田园诗人奈德哈特·冯·罗恩塔尔[1]他却了如指掌。
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个这样的人,伟大诗篇的诗行烂熟于胸,对文艺复兴和超现实主义的名作了如指掌,对哲学史和音乐史如数家珍 —我们把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置于如此境地,在那里他所面对的,要么是证明自己精神的现实性与效力,要么将其看作一无是处,那是一个极限处境,那是在奥斯维辛。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于此。我曾经以双重身份,作为犹太人和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伯根-贝尔森和其他一些集中营,除此之外还在奥斯维辛,准确地说,在附属集中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Auschwitz-Monowitz)待过一年。所以在本书中,只要我愿意的话,“我”这个小词必然常常出现,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将个人经历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
在我们的语境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与所有人,包括那些脑力工作的从业者特有的外部处境。一个糟糕的处境,以极为戏剧化的方式在强制劳动下面临的生死抉择的问题中凸显出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中的工匠,只要没有被以一个这里用不着细说的随便的理由赶进毒气室,就会得到相应的职业分配。比如有个锁匠被赋予了特权,因为当时待建的染料工业集团工厂[2]需要他,他就有机会在有遮挡的、无须暴露在恶劣天气中的工棚里干活。电工、装修工、造家具的和盖房的有同样待遇。谁要是裁缝或者鞋匠,也许就有机会到专门侍奉党卫军的房间里去干活。泥瓦匠、厨师、无线电工人和汽车技师也有*微小的机会,获得一个可以忍受的工作岗位,从而幸存下去。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遭遇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境。等待他的是和商贩一样的命运,他们都属于集中营里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会被分进一个小组,挖坑、埋线缆、搬运水泥袋和钢梁。在集中营里他成了没有职业资质的工人,不得不在野外干活,多数时候这相当于已经对他下了判决。肯定也存在差别。在前面提到的那些集中营里,化学技师仍然能从事他的本职工作,像我的狱友,来自都灵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他写了一本关于奥斯维辛的书《这是不是个人》(Ist das ein Mensch?)。医生也有可能在一个叫作医护所的地方栖身,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如此。例如来自维也纳的医生,如今已是著名心理医师的维克多 ·弗兰克(Viktor Frank)曾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长年挖掘土方。一般而言,脑力劳动者在集中营里的工作处境极为恶劣。许多人因此试图隐瞒他们的职业。谁如果掌握一点小手艺,会做些工艺,就会大胆地装成一个手工匠人。当然,一旦他说的谎暴露出来,就得担上丧命的风险。多数人把自己说得身无所长,想借此撞撞运气。人文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在被问到自己的职业时,会胆怯地说“老师”,生怕招惹党卫军士兵和牢头的羞辱。律师装成普通的书记员,记者可能谎称自己是排字工,在必须提供自己的技能证明时这样做危险较小。大学老师、律师、图书馆员、艺术史学者、国民经济学家、数学家,他们拖拽着铁轨、钢管和木材,大多数时候他们笨手笨脚,体力透支。极少数情况下,苦力劳动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他们被带离工地,送到邻近的主集中营,那里矗立着毒气室和火葬场。
他们在工作场所处境艰难,在集中营里也好不到哪里去。集中营生活首先要求身体矫健和一种必需的、近乎残忍的血性。鲜有知识分子具备这两样长处,而他们经常看重的道德勇气,在这里一文不值。例如说,有一次,要阻止一个华沙的职业扒手偷我们的鞋带,这时候能派上用场的是一记下勾拳,而不是精神上的勇气,一个政治记者会出于这样的勇气发表一篇不受欢迎的文章而危及生命。毋庸多说,律师或者人文中学教师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出一记下勾拳,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挨得拳头远多过他们给别人的,他们更擅长挨揍而非揍人。集中营的纪律问题上也一样糟糕。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一般没什么铺床的天赋。我记得我那些满腹学识、教养良好的同伴,每天早上满头大汗地和被褥搏斗却弄得一团糟,以至于工作时像得了强迫症般担惊受怕,生怕回去后挨揍挨饿。他们既不擅长铺床,也不会机灵地行“脱帽礼”。恰巧碰上狱中年长的人或者党卫军士兵时,他们从来都不会那套几乎卑躬屈膝却又自知自觉的说话方式,学会那样说话有时候可以避开近在眼前的危险。所以在集中营里,囚犯里的头头和室友不尊重他们,在工地上的牢头和工人也瞧不起他们。
更糟的是,他们找不到一个朋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生理上就学不会用集中营里的粗话直截了当地交谈,而这些粗话是唯一被接受的相互理解的方式。人们经常谈到现代的思想争论中存在的同代人间的交流困难,谈到那些突兀的、不如不说的蠢话。在集中营里交流障碍存在于知识分子和他们大多数的同伴之间,无时无刻不以真实、折磨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习惯了细致入微的表达方式的囚犯来说,要努力克服自我才可能说出“滚开!”或者只用“嘿,家伙”跟同伴打招呼。我清楚记得那种身体上的反感,每当一个别的方面都正常、随和的同伴不跟我说别的,只说“我亲爱的男子汉”时,这种感觉就会把我笼罩。知识分子忍受着“伙夫”“整弄”(指非法占有财物)等表达,即便像“运走了” [3]这样的词也要很勉强才会从他们嘴里蹦出来。
哲学/宗教 哲学 哲学知识读物
在线阅读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零零教育社区:论坛热帖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